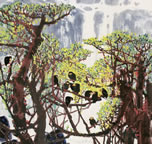|
对新媚俗主义的批判(二)政治的媚俗
文 何桂彦
既然不能对抗体制,那么难道就要向体制妥协?既然走现代艺术的精英艺术之路是孤独的,那么艺术家就只能选择“行画”和“风情画”?当代绘画在这两者之间难道就没有可走的第三条路?“媚俗”或许正是这些选择中的第三条路,即保存自身的某种精英性,又寻求与艺术市场的妥协。同时,此一阶段的媚俗现象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艺术从现代阶段向当代阶段过渡时期的产物。这里有两个时间的分界点。一个是以1989年中国的现代艺术大展为界,前期是以艺术家的个体对抗群体,艺术风格的前卫对抗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对抗保守,由于采用了多元对抗一元、民间对抗官方的精英主义方式,因此,我们习惯将之前的艺术称为中国的现代艺术阶段。一个是大约从1992年开始,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海外市场的成熟,艺术开始进入市场,艺术品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之中。我们习惯将这之后的艺术称为中国的当代艺术阶段。当然,这种划分只是时间上的概念,并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艺术思潮、形态方式、创作观念、审美取向等本质性问题。如果一定要在这种时间概念中找到一种艺术现象的话,那么“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便当仁不让的构成了从现代到当代转向中的转折点。
然而,“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无疑是最早产生“媚俗”趣味的温床。首先来看王广义为代表的“政治波普”。和早期新潮美术那些有着强烈批判性的作品不同,王广义的《大批判》要温和得多,他用了一种官方不至于压制的方式,用调侃、幽默、解构的态度和波普艺术并置的方法来处理工农兵的肖像。显然这是一种与官方的妥协。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否定王广义在创作《大批判》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是说,《大批判》的创作至少是考虑过官方的接受力的。同样,由于他使用了工农兵形象和西方流行文化中出现的可口可乐、万宝路香烟等符号,由于这些图像所暗示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潜在的批判仍保留了八五时期的人文主义色彩。因此,可以说王广义是在打一种“擦边球”,既要保持新潮的批判态度,但又不能太强烈;既要对抗体制,但也不至于让官方太反感。然而,和“政治波普”相比,以方力钧为代表的“泼皮现实”主义则要隐蔽得多。这主要是,90年代初,新一代年青艺术家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崇高理想和秉承的自由艺术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突然坍塌和消解了,至少说进入了沉潜状态。生存的困境、社会价值标准的坍塌、个人理想的消失确实让当时一批年青人把握不住未来的方向。抗争还是消沉,拯救还是逃避,这些矛盾的问题并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答案,于是一种虚无的、无聊的情绪自然成为艺术家们自身现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仍然是一种妥协,一种向政治和向社会的妥协,只不过,这种妥协是穿着从八五宏大叙事向关注自我存在方式转变的外衣而出现的。
实际上,我们对“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史意义仍需要重新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从“后89·中国新艺术展”之后,海外画廊和国际艺术机构对这两种艺术现象的操控和炒作,尤其是赋予它们过多的政治文化内涵,所以,作品在流通过程中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作品在创作之初时的意义,而且更复杂、更多元。如果说,早期的这批艺术家是不自觉的使用或表现了某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图像,那么,在后期的作品中,更为夸张的造型、更为艳俗的色彩、更为强化的个人符号,更为浓郁的政治映射,便是艺术家自觉地对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利用。特别是方力钧后来的“光头”、岳敏君的“大脸”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用批评家王南暝的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趣味。当然,用批评家高名潞的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媚俗”。[⑫]这种媚俗趣味在9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假借政治意识形态和贩卖中国文化符号的作品。具体来看,艺术家们最重要的创作方式是,寻找各种文革的经典图式,如各种传单、批量复制的宣传画、大字报、大标语、经典样板戏的样式和“红光亮”、“高大全”的图像叙事;或者利用各种毛时代的图像符号,如毛**像章、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等。由于这些公共的图像有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其中的文化意识形态性自不待言。当这些图像被艺术家用一种艳俗或波普的图像将其表现出来后,一种泛化的“政治媚俗”由此产生。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这些艺术作品完全没有价值,因为,政治和政治生活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头戏,所以它们的存在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90年代中期国际艺术市场走向成熟这个重要的外部艺术环境,换言之,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作品是为谁创作,为谁消费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媚俗”的趣味?
美国批评家所罗门称方力钧的作品《一个打哈欠的人》为“这不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一声吼叫。”显然,所罗门这里明显存在着文化误读,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已先在的将自己划定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来自中国的方力钧只是一个“他者”,而他的作品只是一个边缘化的参照对象,是对西方或美国的那种“文化优越性”的反证。其实,在90年代初,当时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都不会想到西方人会对“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产生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西方人后来从后殖民或者从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些角度去阐释这些作品。方力钧不会想到,包括批评家栗宪庭先生也没有料得。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艺术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泛政治”化作品在西方人眼中的价值。同样,方力钧在西方的“走红”使其成为其后这一脉络艺术家的偶像。于是,在一个全球艺术市场走向成熟的时候,“政治的媚俗”开始在中国泛滥。同时需要提及的是,这也正是“政治波普”和“政治媚俗”的区别所在。对于前者来说,它有着新潮美术的批判精神,也有着产生它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后者而言,除了是迎合海外的艺术市场的需求外,所谓的批判精神已丧失殆尽。
如果说,“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早期的“媚俗倾向”是一种不自觉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后,“政治的媚俗”便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果说,早期的“政治波普”是在“新潮美术”受挫后向官方的一次妥协的话,那么,其后的“政治的媚俗”性绘画则是向西方的主动“献媚”。而且这种“媚俗”趣味随着90年代中后期全球艺术市场的成熟正在逐渐向中国当代绘画的主流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