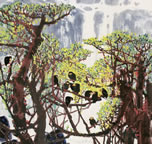|
在体制的墙里墙外再看“技术”
文 陈默
接到编辑约稿,给出艺术的“反技术化”命题。不明理由,遂细读约稿提示,恍然小悟:这是个在不同位置角度会“看”出不同结果的有点变色龙味道的“问题”。这样说的理由是,若把某假定的“问题”,不假思索地随处随意放置,可能会出现是“问题”又不是问题的混乱而滑稽的结果。这里,我们不妨先求证《辞海》查一下何为“技术”:一是泛指根据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二是指除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上述给出的解释,受出版年代以及惯性思维的影响,将“技术”限制于工厂生产和工人的操作能力上。而事实上,技术问题远比《辞海》所谈丰富,所涉及的范围各行各业诸如商场官场情场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我们今天感兴趣的,是在谈与艺术相关的技术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在当代性的语境里,谈“技术”会让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之所以强调在当代性的语境里谈“技术”,是因为在此之外,还有个在体制的温床上惯性几十年形成的“美术”语境。几十年的复杂成因积累,它已然形成一道厚重的“墙”。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理由和规则谈“技术”。这里所涉及的“美术”,已不仅仅是指在传统意义上的“国、油、版、雕、工艺”范畴。在更大的框架内,它还包括与体制同步的行业制度管理层面,以及与其相关的有充分保障的既得利益层面。在这样的利益集团范围或曰“墙内”谈“技术”,就得尊重此范畴内的相关规则。首先,它要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遵守基于写实要求的一元的审美制度,以及围绕此制度衍生的思想及技术方式。在思想上,应充分贯彻“真、善、美”的判断作品质量优劣的“惟一”标准,作品的生活性、对象性、写实性,是每位从业者务必要牢记的。在技术上,对形象、形态、构图、细节的精致把握与刻画,乃是考量从业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上述所谈的“技术”,实际包含了思想和制作两个方面。任何艺术形态,概莫能外。
回到当代性的语境里,亦即在体制的“墙外”谈“技术”,与“墙内”的情态有着显著差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现当代艺术同时登陆本土,也意味着长达二十余年的在体制外的新锐艺术的艰苦跋涉的开始。这是个弹性与张力很大的群体,他们没有体制化的行业制度管理,当然也失去了体制的呵护和有保障的既得利益。与体制的“墙内”有着相应的规则一样也不一样,当代艺术的“规则”呈现着模糊而鲜明的特点。首先,站在与传统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平台上,并在充分尊重艺术家表达自由的前提下,强调表现的多元和审美的多元。用丰富的新艺术语言,最大可能地将新思想、新观念、新图像予以表达释放。反复制、排它性、独立性、异常性、观念性,甚至是破坏性,都可能成为艺术家们常用的“技术”。而围绕上述思想“技术”产生的制作“技术”,则会因作者的趋向,作品的要求,现场的要求,材料的要求,视觉的要求等等,出现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细节、精致、到位、严谨、准确等因素,是技术的中枢。在这里,评判“技术”的好坏,只能以对作品的表达程度的高下而论,不可能脱离作品空谈。
如是,在“墙外”与“墙内”大不相同的背景和差异甚大的语境里,讨论艺术的“反技术化”命题,的确有些左右为难。就“墙内”而言,成型于上世纪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贯穿至今的意识形态化的审美和创作模式,并没有尊重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发展原则,而是在复古僵化的泥潭内难以自拔。这也就不难怪,时至当代文化迅猛发展的今日,还要错觉地以几十年不变的老尺度来衡量今天的事物。而事实是,“墙内”的利益集团,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弱化风光不再;“墙外”昔日的小草,已自在长成参天大树。在说“反技术化”问题之前,应该弄清楚问题对象及所处在的社会背景。至少,不可能退回三十年,并用“惟一标准”来评说优劣。我们既反对打着当代的旗号鱼目混珠,也反对思想与表达的脱节错位,更反对架空技术的反技术现象。在当下,的确存在不少“技术”过硬思想受潮的老艺术家,也有不少思想新潮“技术”偏弱的年轻艺术家。“技术”“功底”,不管是在过去的“墙内”,还是在今天的“墙外”,从未失去过重要性。只不过,应该下力去矫正那种教条八股的唯功底是瞻的空泛主义。功底也好,技术也罢,恰当为好,够用是上。关键是,在流动发展的文化脉络里,看事物的眼睛也要顺势而为不断更新。如此,才不会为问题所困,才会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中获得进步。
|